
文:宋知夏
來源:三聯(lián)生活周刊(ID:lifeweek)
2024年,社交媒體上“離職博主”的賽道突然變得擁擠。“媽媽,人生是曠野”,在這句現(xiàn)象級(jí)流行語的鼓舞下,年輕人裸辭、GAP、當(dāng)起數(shù)字游民,奔向充滿自由誘惑的遠(yuǎn)方。
然而,短暫逃離現(xiàn)實(shí)后,生活仍然繼續(xù)。隨著“第一批離職博主集體上班”,許多人又重新回到日常的軌道,過去懸而未決的問題再次撲面而來。超負(fù)荷的工作、快節(jié)奏的生活、無法排解的孤寂,讓年輕人喪失了幸福的能力,周身散發(fā)著“淡淡的死感”。
都市里的年輕人該如何自救?早在2019年,人類學(xué)者項(xiàng)飆就建議,年輕人可以通過發(fā)現(xiàn)“附近”來構(gòu)建自己的現(xiàn)實(shí)感。放下手機(jī),去關(guān)注身邊500米范圍內(nèi)的草木、人事,以擺脫孤獨(dú)與不安的根源——虛擬性帶來的懸浮感,找到生活的穩(wěn)定性和意義。
五年后的今天,“附近”這個(gè)概念的含金量仍在上升。
01
成為孤島的
都市人
失去“附近”,于都市人而言,像一場無法逃脫的命運(yùn)。
早起,擠地鐵,應(yīng)付工作,被迫加班,漫無目的地刷手機(jī),熬夜。很多人的一天就在這樣的節(jié)奏中流逝。疲憊、機(jī)械、麻木,又孤獨(dú)、失落、無力。無暇關(guān)注周圍的細(xì)節(jié),找不到人生的意義,也無從心生喜悅。
于是,被困住的都市人總想逃離,周末進(jìn)山里,假期赴遠(yuǎn)方,依靠短暫的離開,去別處尋找能量。
人類學(xué)者項(xiàng)飆認(rèn)為,這正是現(xiàn)代社會(huì)“附近”消失的一種表現(xiàn)。人們?cè)絹碓酵ㄟ^抽象的概念和原則來理解世界和生活,卻忽視了周邊具體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于是鄰居成為陌生人,虛擬的社交網(wǎng)絡(luò)成為情感支點(diǎn)。
有越來越多的社會(huì)學(xué)、心理學(xué)研究發(fā)現(xiàn),社交網(wǎng)絡(luò)的普及,雖然縮減了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但同時(shí)也促成了人的“原子化”,讓人失去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歸屬感,從而讓孤獨(dú)變得更加真實(shí)和強(qiáng)烈。頻繁刷手機(jī),內(nèi)心卻空空蕩蕩,成為許多人的通病。
在項(xiàng)飆的定義中,“附近”不僅僅指物理上的距離,它還包含了很多細(xì)密的、復(fù)雜的、容易被忽視但實(shí)際上非常重要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附近”能夠幫助人們重新樹立一種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更好地欣賞、讀懂社會(huì)的差異性;同時(shí),還可以幫助人們從“時(shí)間的暴政”中解放出來,重構(gòu)自己的生活。
?
現(xiàn)代東方茶品牌霸王茶姬也觀察到了當(dāng)代年輕人的困局,以專屬秋季的桂花香為靈感,推出全新主題包裝的桂馥蘭香,邀請(qǐng)茶友們一起愈秋同游,共尋身邊治愈力。

霸王茶姬本次還特別聯(lián)合《三聯(lián)生活周刊》,特邀中國人民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副教授董晨宇,青年藝術(shù)家張大強(qiáng)(自媒體賬號(hào)“張大強(qiáng)的白日夢”主理人),和《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主任記者魏倩,從對(duì)談出發(fā),在深入剖析了數(shù)字時(shí)代的“附近”是如何丟失的,以及社交媒體如何改變了大家對(duì)真實(shí)生活的感知的同時(shí),我們也想試著以一種自然、開放的心態(tài)去感受和參與生活,發(fā)現(xiàn)治愈與驚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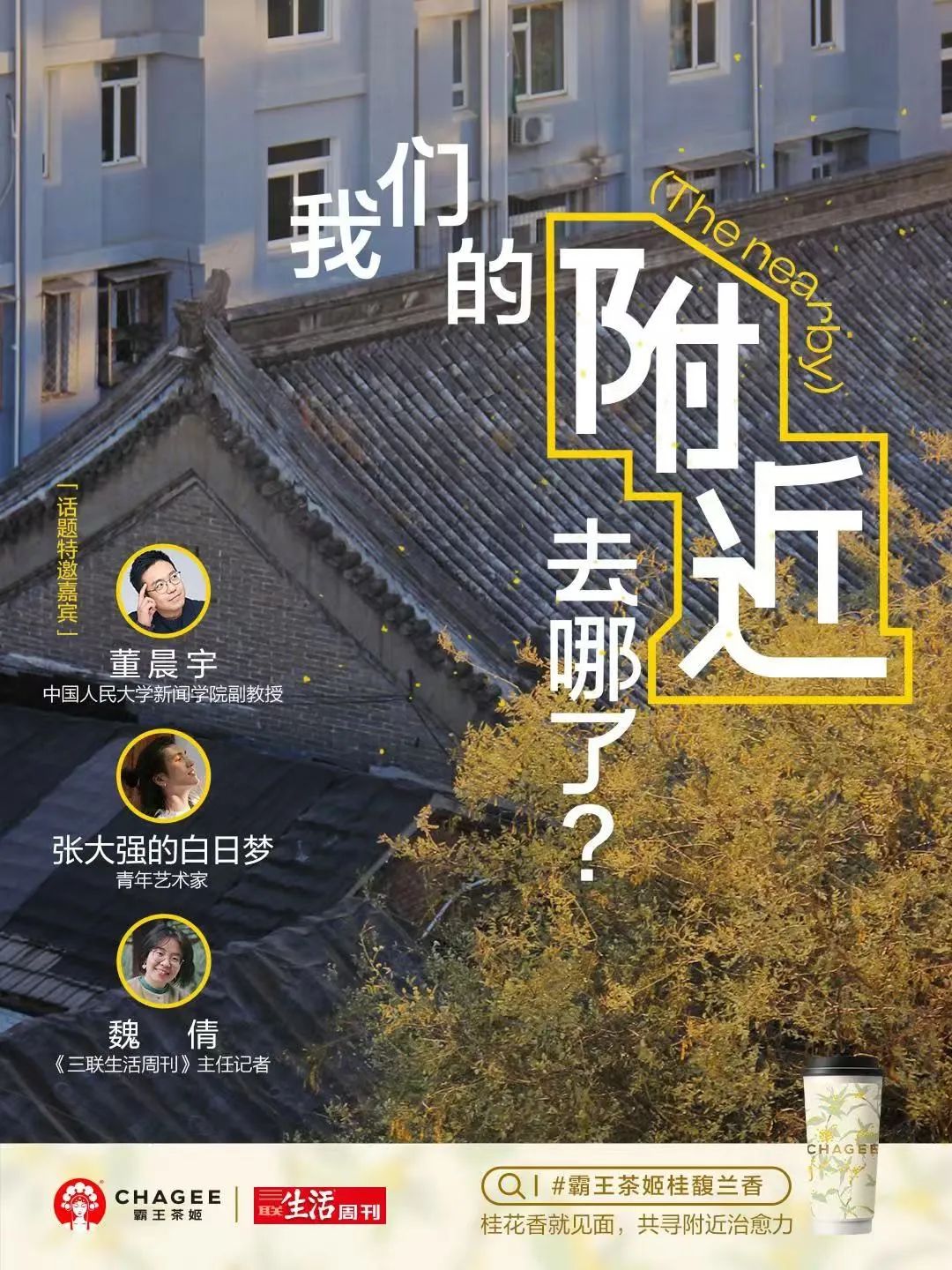
02
一百個(gè)點(diǎn)贊抵不過
一個(gè)真實(shí)的擁抱
在此次關(guān)于“附近”的探討中,董晨宇認(rèn)為,互聯(lián)網(wǎng)的價(jià)值之一,是帶給了我們數(shù)字“附近”,但它仍然無法取代體驗(yàn)充盈的真實(shí)的人之間的相遇。
人需要活在人群中,這是刻在我們DNA深處的自然屬性。無論網(wǎng)絡(luò)多么發(fā)達(dá),技術(shù)如何先進(jìn),線下的交往都無法被取代。
早在2008年,芝加哥大學(xué)的學(xué)者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就對(duì)不同的社交方式(社交媒體臉書、論壇、在線游戲、約會(huì)網(wǎng)站及線下面對(duì)面的社交)進(jìn)行了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一個(gè)人線下(面對(duì)面)與他人互動(dòng)的比例越高,就越不容易感到孤獨(dú)。
近幾年,類似的發(fā)現(xiàn)在全球范圍內(nèi)都有。在德國著名記者、作家伊麗莎白·馮·塔登所著的《自我決定的孤獨(dú)》一書中,無論是哲學(xué)家、宗教學(xué)家還是心理學(xué)家,都有一個(gè)共通的結(jié)論——
“虛擬的存在永遠(yuǎn)無法替代真實(shí)的身體接觸……眼神、聲音、相遇、關(guān)系、觸碰,這些才能夠使我們獲得自由。”
生活在上海的街頭行為藝術(shù)家張大強(qiáng)對(duì)這一點(diǎn)很有發(fā)言權(quán)。他第一次走上街頭的契機(jī),是去年夏天剛剛搬到上海時(shí),產(chǎn)生了一種無法抑制的孤獨(dú)感。那段時(shí)間,他住在偏遠(yuǎn)的郊區(qū),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將如何展開,常常望著窗外的藍(lán)天、白云、麥田陷入沉默。
一天傍晚,他突然覺得自己就像一片云,在這個(gè)大都市居無定所、漂泊無依。“會(huì)不會(huì)其他人也和我有一樣的感覺?”張大強(qiáng)決定鼓起勇氣,試著把自己變成一朵云,走上街頭,并邀請(qǐng)陌生人和他一起,戴上云朵狀的頭套,做一朵“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說話”的云。

在上海街頭邀請(qǐng)你們和我一起當(dāng)一朵云
@張大強(qiáng)的白日夢
很快,人們駐足在張大強(qiáng)的周圍,好奇地打量、拍照,也有人戴上頭套,坐在他的身邊,無聲地和他共創(chuàng)了這個(gè)作品。這次體驗(yàn)讓張大強(qiáng)打消了對(duì)街頭行為藝術(shù)的排斥和心理障礙,真實(shí)的觀眾回應(yīng),回饋給他巨大的創(chuàng)作動(dòng)力和源源不斷的靈感。
街頭行為藝術(shù)的魅力,在于讓城市的街道暫時(shí)變成沒有圍墻的劇場,每一位過客都是潛在的觀眾,也是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藝術(shù)作品搭起一座橋梁,讓忙碌的行人停下腳步,讓陌生的目光產(chǎn)生交匯。
在項(xiàng)飆關(guān)于“重建附近”的闡釋中,與身邊的陌生人產(chǎn)生連接,是現(xiàn)代人應(yīng)該學(xué)習(xí)一個(gè)課題。作為“附近”中關(guān)鍵性的一部分,陌生人是日常生活的動(dòng)力來源:外賣員、保安、小區(qū)里的鄰居……這些人維系著城市和生活的運(yùn)轉(zhuǎn),卻被我們有意無意忽略。
了解身邊的陌生人,關(guān)注陌生人,不僅是重新發(fā)現(xiàn)“附近”與城市生活的過程,更是重新打量個(gè)體與社會(huì)共同體關(guān)系的途徑。當(dāng)個(gè)體對(duì)社會(huì)的了解更加豐富,也會(huì)擁有更多具體的勇氣,去面對(duì)各種具體的困難。
張大強(qiáng)正是在一次次與陌生人的相遇中,獲得許多的滋養(yǎng)和樂趣。去年秋天,張大強(qiáng)曾帶著透明的“垃圾桶”走到上海街頭去“收集秋天”。他把落葉從環(huán)衛(wèi)工人的黑色塑料袋中“搶救”出來,也特別留意收集飄落的桂花。

在上海“收集秋天”
@張大強(qiáng)的白日夢
張大強(qiáng)邀請(qǐng)經(jīng)過的行人加入自己,許多老人、孩童非常喜歡參與這個(gè)活動(dòng),在撿拾落葉、細(xì)嗅桂花的過程中,人們分享著彼此對(duì)秋天的記憶和情感。在這個(gè)溫暖、多彩的場景中,他們內(nèi)心的愛和喜悅都自然生發(fā)出來。
?
“互聯(lián)網(wǎng)上一百個(gè)點(diǎn)贊,抵不過一句當(dāng)面的鄭重感謝,更無法替代一個(gè)真實(shí)的擁抱。”董晨宇認(rèn)為,社交網(wǎng)絡(luò)是人與人相遇的權(quán)宜之計(jì),年輕人可以試著創(chuàng)造更多線下交往的機(jī)會(huì)。
比如,在這個(gè)秋天去和朋友見面,點(diǎn)一杯帶有桂花香氣的桂馥蘭香,把手機(jī)調(diào)靜音,觀察正在變黃的樹葉,或展開一次深度的對(duì)談;又或是出門去小區(qū)周邊走走,看看平時(shí)匆匆經(jīng)過的小路藏著哪些驚喜。
 大覺寺的銀杏樹 | 魏倩拍攝
大覺寺的銀杏樹 | 魏倩拍攝
03
關(guān)注身邊500米,
重拾“附近”
項(xiàng)飆在提出“附近”的概念時(shí),主張年輕人應(yīng)該關(guān)注身邊500米范圍內(nèi)的草木、人事。當(dāng)有人聽從建議,決定走出房間,神奇的改變發(fā)生了。有人不再遠(yuǎn)行,放棄短暫的逃離,因?yàn)殛P(guān)注樓下的花、路邊的樹也能帶來樂趣;有人發(fā)現(xiàn),下班回家前和樓下小店的老板聊聊天,竟能緩解一天的煩躁和疲憊。
住在上海的小紅書網(wǎng)友@Buzzbuzz 走出房間后,“看到紫色的云,看到附近的荒草,看到夕陽下金色的小狗”,她“和早餐店拿起糯米團(tuán)子的老奶奶聊天,觀察寺廟外河邊的背包客,見自己的朋友”,感到一種“久違的、具體的自由”。而小紅書網(wǎng)友@大力阿七 則從一個(gè)“世界青年”突變?yōu)椤叭f年場人”。她不再總往外跑,活動(dòng)半徑就在家附近3公里之內(nèi)。她現(xiàn)在更加確信,相比“此刻很投緣,但再也不相見”的一次性相遇,和樓下雜貨店老板聊天、和路邊歇腳的鄰居老奶奶嘮嗑,更讓人安心。“短暫的逃離沒意義,不如找到「我住在這里的理由」。”
在這個(gè)金秋,霸王茶姬也發(fā)起了“桂花香就見面”的活動(dòng),鼓勵(lì)茶友在這個(gè)適合見面的日子,約上好友,走到戶外,去感受真實(shí)的生活,發(fā)現(xiàn)“附近”的美好和治愈。在投稿中,小紅書網(wǎng)友@川鄉(xiāng) 的秋日治愈時(shí)刻,是在院子里的藤椅上不小心睡著,醒來發(fā)現(xiàn)“眉間,發(fā)里,躺椅里,藍(lán)色茶杯里,白色衣服的褶皺里…都落滿金黃的桂花。感覺自己被香氣擁抱著,陶陶欲醉。”微博網(wǎng)友@歐雪菲蒙 認(rèn)為,我們無法改變環(huán)境,卻可以看見身邊的人和事,“找到生活的根兒,活得才有味兒,這才叫活明白了”;小紅書網(wǎng)友@康康 總會(huì)在北京的秋天思念蘇州軟軟糯糯的桂花香,這個(gè)味道陪伴了她的高中生涯,她說“捧著霸王茶姬的桂馥蘭香,總能讓我回憶起那段燦爛的年少人生”。
越來越多的人們正在渴求找回“附近”,他們?nèi)ity walk,去感受“公園20分鐘效應(yīng)”,?試圖在城市中尋找一個(gè)小小的居心之所。在選擇旅行目的地時(shí),也有更多人避開熱門景點(diǎn),轉(zhuǎn)而去有煙火氣的小地方,去從他人的日常中獲得能量。
董晨宇最近剛剛結(jié)束了一段在福建的旅行,他住在當(dāng)?shù)厝说木幼^(qū),感受當(dāng)?shù)氐拿朗澈蜕罟?jié)奏,感受到一種深深的滿足感。有一天他乘著竹排游江時(shí),船夫大哥突然感嘆“今年的桂花香來得晚一些。”董晨宇這才知道,當(dāng)?shù)厝丝梢悦翡J地通過桂花香的氣味來判斷冬天的冷暖,他們身上有一種與自然連接的能力,而長期在都市居住的人,可能已經(jīng)喪失了這種感知力。
回到北京后,董晨宇開始像一個(gè)朋友學(xué)習(xí),“有困惑,就出門”,打開自己的所有感官,去接觸自然、去和人見面、去現(xiàn)實(shí)世界里尋找答案。他越來越感覺到,“無名的附近比著名的遙遠(yuǎn)更舒服。”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主任記者魏倩也在有意識(shí)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她開始盡量避免坐地鐵,而用坐公交車、騎行或步行替代,以此獲得更多觀察外部世界,與他人經(jīng)過、接觸的機(jī)會(huì)。

張大強(qiáng)則更加確信,面對(duì)面的交流才能有效打消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在過去一年,最讓他感動(dòng)的時(shí)刻正是發(fā)生在街頭。一次展示作品時(shí),一位大叔聽完他解釋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后,鄭重地對(duì)張大強(qiáng)豎起大拇指,并說:“我以前覺得你們這類人是在嘩眾取寵,但你讓我對(duì)這個(gè)群體有了新的認(rèn)識(shí)和改觀。我覺得你這個(gè)作品非常好,很有意義。”
經(jīng)過此次和董晨宇、魏倩的對(duì)談,張大強(qiáng)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人與人之間失去了摩擦力”這個(gè)觀點(diǎn)產(chǎn)生了興趣,或許,未來他會(huì)就此創(chuàng)造出新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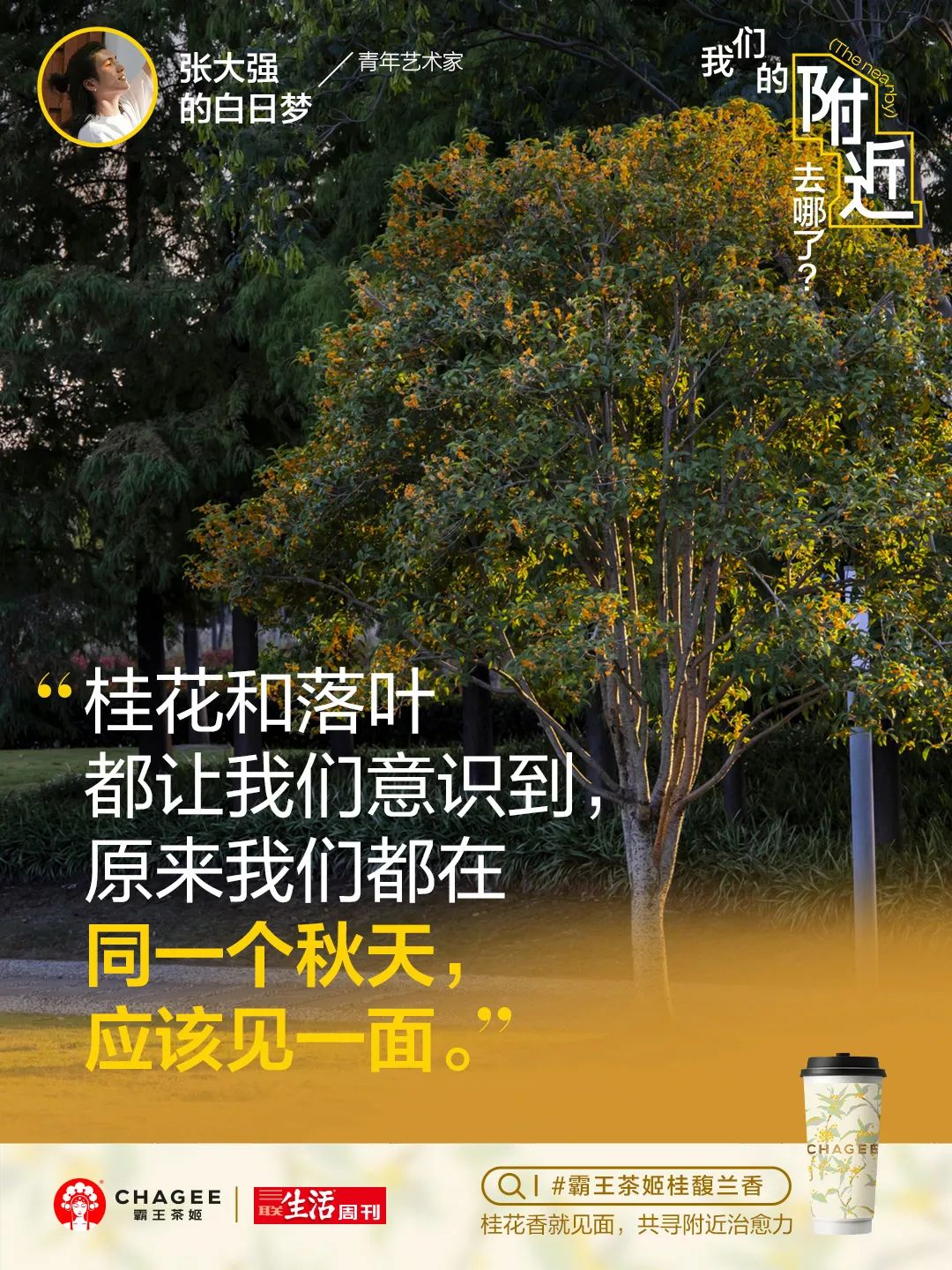
每個(gè)人都不是一座孤島。我們需要他人,也需要“附近”。作家毛姆曾經(jīng)說過,“一個(gè)人能觀察落葉,鮮花,從細(xì)微處欣賞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樣。”
希望霸王茶姬和《三聯(lián)生活周刊》能夠帶給你一點(diǎn)啟發(fā)、一份治愈。如果你因此萌生了去探索“附近”的沖動(dòng),請(qǐng)勇敢地走出房間,去觀察、去關(guān)心、去釋放善意,相信你會(huì)有不一樣的體驗(yàn)和收獲。
秋天桂花香時(shí),帶著桂馥蘭香,去和想見的人見面吧。換一種活法,或許,生活的意義就是當(dāng)下,就在“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