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羅曉蘭 解亦鴻 楊粟予
來源:極晝工作室(ID:media-fo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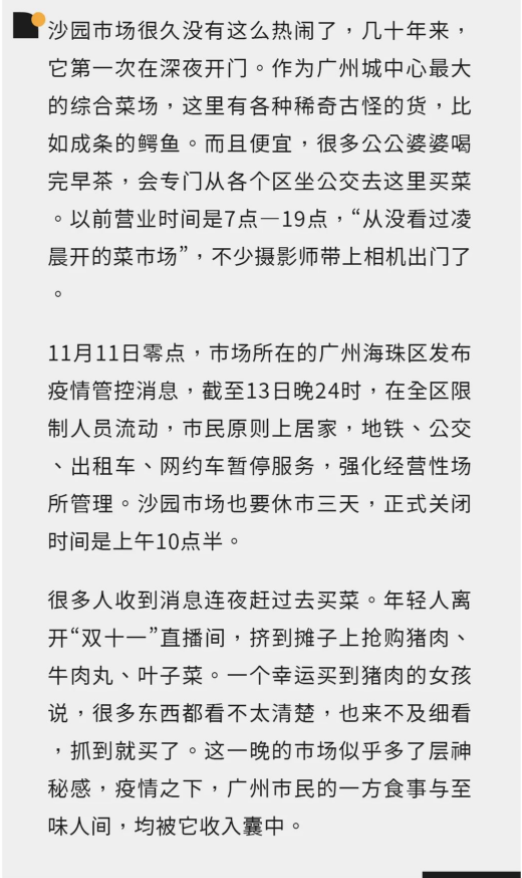
01
預售的豬肉
豬肉遲遲不來,十多個檔口,每一個都排了近10人。一個會做生意的老板打出了廣告牌,“等下有新鮮豬肉賣,三點到。”不少人都看到了他,一個穿著黃色上衣的中年男人,廣告牌是塊白色泡沫板,還粘著一片未撕凈的膠帶。他用粵語叫賣“就快到!就快到!”說著扯下口罩,左手點了根煙,右手還舉著泡沫板,不時晃晃。
攝影師韓冠聲拍下了這個獨特的廣告牌,不時有顧客過去問,是不是真的三點有豬肉啊?黃衣老板有些得意:“對啊,我們是最早有豬肉的,你就等一下咯。”
凌晨3點左右,雞鴨肉鋪基本賣空了。豬肉還沒到,老板們不斷打電話催,“車到哪里了?”“什么時候到?”圍裙和手套早早戴好,磨刀棒和四把刀擺在案上——大小不同的刀,分別砍不同部位,掛肉的鐵鉤也已擦亮。
廣州人喜歡用鮮肉煲湯,而且吃得講究,要分上肉、瘦肉、五花、梅柳等。黃衣老板拿出紙,讓顧客提前登記需求:要幾斤,什么部位?半小時后,肉廠的貨車一過來,人群立刻湊了上去,韓冠聲也擠到車門前拍照。卸貨,裝車,分貨,男人們等不及小推車,直接將整只豬扛上肩,沖到攤位上。
剛切下一塊,還沒去皮切片,就有人指著說“這塊我要了”,老板看到誰就給誰。因為順序的先后,顧客間起了小摩擦,但嘟囔幾句,就趕緊搶下一塊了。

●黃衣老板豬肉攤打出的廣告牌,不同人輪流舉著。攝影/Pingolau 劉
中年女士Sandy湊到豬肉攤前,立刻引起人群的憤怒:“排隊啊!排隊啊!”她連忙解釋:“我不是買,先問下價格。”她常去沙園市場,黑土豬平時賣30多塊,此刻普通瘦肉賣到了68塊。她往里走,看到也有賣39塊多的,但摻了些不太好的部位。
即使漲價,很多人還是在排隊等這一晚的新鮮豬肉。商家雖然手腳快,但人一多,沒法像平時切得那么干凈,“這里砍一塊,那里砍一塊,砍、砍、砍,就給你的咯,平時搞得很干凈。”Sandy覺得質量一般,只買了三四根排骨,但她的朋友沒管價格,買了整整一排,花了五六百。
前一天下午,Sandy家的米吃完了,她在網上訂了一袋,平時一小時能送過來的,到了晚上八九點才到。她打電話問了外送平臺,貨源還比較充足,但快遞送貨的人太忙了,比往常要慢,接近零點,收到了管控消息。
這個時間點也剛好是“雙十一”活動的最后一天,Sandy早就把要買的東西加入了購物車,只等最后付款湊滿減。弄完剛準備睡覺,朋友突然打電話叫她去買菜,催她說“明天就沒得買了”。
Sandy不是喜歡囤貨的人,但白天買米等了很久,又想到孩子在上網課,一天三餐都得在家吃,就去了市場。她所在的海珠區,因人口密集,成為廣州本輪的防控重點。不止一名去搶購的顧客提到,近幾日,網上買菜品種不全,還得拼手速,一早就開搶,到了中午可能就會斷貨。
凌晨2點半,人越來越多。潮汕牛肉丸店的老板娘或許是在睡夢中被叫醒的,她小跑著趕來,背包還沒放下,就從冰箱拿出了存貨。另一家凍品鋪的魚皮餃,還沒從冰箱里全擺出來,顧客就拿起小鐵鏟子自己裝袋,若不是做好了付錢的準備,老板甚至有點害怕,“土匪打劫一樣”。
女生張雪先去買了雞胸肉,又在凍品鋪買了兔腿,都是給“叮叮”囤的貨。“叮叮”是一只拉布拉多,平時會跟著張雪一起出“車尾攤”,賣爆漿雞蛋仔——張雪老公以前做地產,現在轉行擺攤,每天收入在100-1000元不等。出攤時,“叮叮”和她的另一只金毛會像攤主一樣,站在車旁守候,在江南西成為很受歡迎的明星狗。
知道深夜開市的消息時,張雪正無聊地刷手機。兩只狗也醒著,它們很親主人,她不睡,狗也不睡。養狗群的朋友發來視頻:沙園市場怎么開了?她看到消息也有點緊張,“怕這次要很久”,趕緊和老公出門買菜。
在凌晨的沙園市場,她有了一種過年的感覺。很多人說,“人山人海,好似行花街咁”——逛花街,新老廣州人最有認同感的傳統文化,這三年沒了,大家惋惜。張雪排隊買云吞,老板包得很快,排隊的人們卻在閑聊,“不如買一點皮子自己回去包,反正關在家很無聊”。最后在水果攤,她也沒忘了給“叮叮”囤幾顆雪梨。

●11月11日凌晨的沙園市場。攝影/Pingolau 劉
3點,沿中心過道的店鋪亮起白熾燈,猶如白晝。隔著口罩,腥味還是撲面而來。螃蟹爬過案板上的支付碼,剛砍斷的魚頭,嘴巴還在一張一合。寵物狗趴在豬肉檔前,伸出舌頭哈氣。摩托車不時鳴笛,“噔噔噔”的切肉聲此起彼伏,一個男中音在叫賣,“靚嘢(好東西)啊,十三蚊(元)啊”。電瓶車從人群里硬擠過去,身后響起抱怨聲:你的車弄到我了!——ok,ok,走走走。
和往日聚集的阿公阿婆不同,這一晚多是年輕人,衣著隨意,邊走邊聽手機,有女孩穿著球褲和拖鞋就來了,背著大挎包。很多人下了車顯得手足無措:“我們要買什么啊”,逮住年紀大的人就問,“魚在哪里買”。
25歲的本地女孩張瑩瑩4點半才到,很幸運地買到了豬肉和一只雞。那時,被挑剩的菜葉已經成了商品,蔬菜檔口前有牌子豎著,“賣菜葉,2.5元一斤”。廣東人的餐桌上每頓都少不了葉菜,炒葉菜,炒菜心、芥蘭,幾乎家家必備。
青菜是最早賣完的,沒到天亮就搶光了。檔口剛把菜拿出來,人群就涌上去,兩斤、三斤的往袋子里裝,連紅薯芋頭都搶。除了辣椒,有顧客說,“這是我們廣州人最后的倔強”。
02
“上帝”要買菜
凌晨四點左右,吳天明坐在空空的攤位前,看著別人的豬肉鋪人來人往,羨慕又著急。他的肉還沒到,貨從番禺區送出,進不來海珠,在路上繞了幾個小時。他給送貨的人打了十幾個電話催,都沒接通,他想,對方肯定嫌煩了。
“關得太突然了。”夜里12點半,他在睡夢中接到送貨人的電話,問貨還能送到嗎?他驚醒,才看到群里通知說要休市3天。錢已經付了,貨進不來,一天還有四五百的攤位費要付。
攤子在市場的南北中心過道上,地理位置好,吳天明想應該能賺些錢。沒想到剛開一年就遇上豬瘟,轉年又來了疫情。在他的印象里,這幾年,顧客明顯變少了,市場里豬肉檔口空了十幾家,有人來試營業,干了幾個月不賺錢就走了。生意好的時候一天能賣4條豬,現在只能賣1條。
當黃衣男人的豬肉鋪變成“網紅景點”時,,吳天明打給送貨人的電話依然沒通——早在零點,就有攝影師記錄下鶴洞大橋上警燈閃爍的一刻,交通錐擋在路中央,車輛接連被攔下,兩區之間已無法通行。吳天明介紹,豬肉廠大多在其它區,送貨的車被擋住,只能繞路,尋找還能過的地方;豬肉遲遲不來的另一個原因,在于豬肉檔第一次在凌晨開門營業,得和肉廠協調時間。

●11月11日零時,兩區之間已無法通行。攝影/Pingolau 劉
先拿到肉的攤位上,小喇叭里不時傳出“微信收款xxx元”。以前顧客是按兩賣,現在有人直接扛走一條豬腿。有閑逛的顧客陪著沒等到貨的老板一起抱怨,“每一分鐘都是錢,錢就這樣飛走了。”賣豬肉的散戶從外面趕過來,見攤子售空了就搬來自己的貨賣,有排骨漲到了88元一斤,“拼命叫(價)”。
吳天明只能干坐著,他鮮少熬夜,上一次還是今年夏天,老年癡呆的母親去鎮上趕集,迷了路,他發朋友圈找人,一夜沒睡。父母都快八十歲了,跟著兄弟在廣西老家生活,40歲的吳天明除了養家,每月還要寄給他們生活費和醫藥費。來廣州打拼20年,他還沒扎下根來,8年前到沙園市場豬肉檔打工,2018年接手檔口,借錢付了5年租金,每月12500元。
檔口費是攤主們不可忽視的一筆支出。賣凍品的王威對各家生意盈虧如數家珍:他對面的,五年交了100萬檔口費,還沒搞什么錢回來;隔壁賣魚老板的女兒,最近開始賣豬肉,十幾萬的成本賣了三個月,全虧了;第七檔的兩公婆花十多萬元請工人、交檔口費,最近一個月白干。
這一晚,王威收入一萬三千元,雞翅、圓仔(牛肉丸、豬肉丸)一個小時就賣光了。這樣的 “好市”,他已經很久沒遇到過了。沙園市場位于8號線和廣佛線的交匯處,曾經是海珠區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后來工業浪潮褪去,人們留在了周圍安居樂業。在這里20年,王威依然堅持一種老派的做生意方式,不送貨、不網購。
只要開市,他就每天凌晨4點去進貨,7點擺貨。擺貨也沒有什么順序,冰箱打開,最上面一層是什么就先擺什么。10平米不到的小鋪,兩臺冰箱,一周七天,如此往復。他心里清楚,現在的人都喜歡網購,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搞,“那都是大老板才搞的東西”。圓仔也是這幾年才開始賣,“年輕人喜歡快,圓仔用電爐泡一下就好了啦。”
這兩年的生意令他失望,“沒錢賺,虧錢。”王威計劃等兒子明年高考完,就和老婆一起回云南老家。他說,對廣州沒有什么留戀的,盡管和老婆在這里相識相戀,往事他不愿多提,笑著說“現在天天吵架”。

●剛運到市場的豬肉。攝影/Pingolau 劉
其他攤主也提到休市會虧錢,就算漲50%也會虧,“三天的店租、員工,還有運營費,太貴了。”同樣賣凍品,25歲的梁龍的運營費是1000多元一天,“每天一睡醒就損失那么多錢。”最近一個月,先是新的貨物調不進來,現在沙園市場休市,清貨也清不掉,兩頭為難。
豬肉攤主在梁龍看來更值得同情,“單價賣得貴一點,但也補不回來這幾天的運營。”為了多賣貨,他一直營業到上午10點半市場停業。之后梁龍才意識到,封區了他出不去,回不了家,只好借住在市場旁邊的店里。
11日凌晨,鱷魚肉、鮮花、桶裝醬油……各種東西都擺了出來,但這些無人問津。草菇平時10多塊一斤,現在降價到7塊了,老板說,貨物得清理掉,“如果等一周就完了”。同樣降價的還有海鮮,有顧客記得,“大閘蟹15塊一只任選,還有帶子、蝦那些,全都是特價出。”海鮮不賣出去,更要放壞了。
此時定價“全憑良心”,一個女顧客介紹,大部分商家沒漲價,也有抬價的,平時四五塊錢的絲瓜、黃瓜賣到10塊錢一斤,大家仍然搶著買。沙園市場門口,“顧客永遠是‘上帝’”的紅色牌子被照亮,攝影師韓冠聲路過時想,上帝要買菜,攤主們就深夜回來營業了。

●市場里的海鮮攤主。攝影/Pingolau 劉

●海鮮水產區附近。攝影/Pingolau 劉
02
人間之味
到了四五點,人潮漸漸從市場退去。地上多了不少搶購完的白色塑料袋,腳印交疊,積了淺淺一層黑泥,變得泥濘。全職媽媽李麗來晚了,有孩子之后,她很難一覺睡到天亮,女兒喜歡踢被子,她就養成了半夜突然醒來的習慣。4點,她看了一眼朋友圈,發現街坊都在買菜,也趕緊去囤貨。
到廣州十多年,她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廣州圖書館,帶孩子去的,那里有一個專門讀繪本的區域。女兒上小學二年級,這是停課后的第三個星期。她每天在家陪女兒上網課、輔導作業、下載課件、“什么都做”。李麗有許多擔憂,一家三口住在沙園市場周邊,靠近更嚴重的康樂村,女兒何時開學依然未知。
早晨買菜回來,她也睡不著了,給女兒做了豬雜粥,沒放綠葉菜——在市場沒搶到,她最喜歡吃的豆腐、白蘿卜,也都沒買到。她沒心思繼續睡,家附近除了比較大的超市,很多街鋪不開了,有街坊仍在慌著買吃的。
凌晨4點才到市場的還有廣漂男孩李海明。他最想買的是幾個大蒜,家里沒蒜了,炒菜不香。豬肉搶購也參與了,他擠進一家人少的攤位,“排骨88元一斤,五花75元。”排隊好不容易輪到他,前面的大哥把肋排都買完了,李海明只好隨手指了一塊五花肉,要兩斤,一刀下去,175元。
他不喜歡這種購物體驗,平時吃外賣多,不經常煮飯,就想買點趕緊走,他問老板“還有排骨嘛”,問了三次,老板都聽不見。
李海明一年沒工作了,炒股也虧錢了。他是湛江人,大專第二年退學,前些年到廣州做服裝批發。實體生意節奏快,幾乎沒有休息,疫情之前,服裝市場基本沒停過。有一年,媽媽在廣州做手術,他卻沒辦法去陪她,“沒人替我”。李海明很喜歡踢足球,邊后衛,以前會開車四五個小時,特地到廣州看恒大的比賽。
但工作忙的時候,趕時間,經常下午才吃第一頓飯,回到家直接在沙發睡著。長年缺覺,“我在天體(天河體育中心)看球幾萬人能睡著”。他覺得將來不會留在廣州,“有可能是因為我買不起這里的房子,也沒資格買”。

●深夜不睡去菜市場的人。攝影/Pingolau 劉
早上9點左右,市場里開始放廣播,通知“即將關閉,只出不進”,社區工作人員在門口疏散人群,廣西人貴哥在這天第三次走進沙園市場。
第一次他在睡夢中被老板叫去買菜。貴哥36歲,為了還債來到廣州打工,在附近市場賣手撕雞。生活很簡單,他和工友同住在宿舍里,早上7點多起床,踩共享單車10分鐘到檔口,晚上下了班去散散步,在路上錄個視頻,發到抖音上。他聽說做抖音直播很賺錢,正在學。沙園市場就在他住的附近,凌晨2點去的時候,他隨手錄了段視頻,居然有將近10萬人瀏覽。
但錄像的那一會兒功夫,菜就被搶光了。第二次再去人更多,他擔心發生踩踏事故,就回去睡覺了。早上起來,他出門做核酸,又想再去錄一段市場關閉的視頻。他初中輟學到廣州打工,做生意欠了債,躲回了老家。今年重來廣州,幸運地找到賣手撕雞的工作,廣州人愛吃雞,包吃包住一個月能有5500,他覺得收入不錯,已經做了六個月。但是最近,他所在的市場關了兩次,解封才可以正常上班,才能有收入。
“我們要快點出去工作。”另一個顧客說,這是所有海珠人的愿望。他和七八個人合伙開了家工作室,承接商業攝影,以前各地出差,隔一天就換個城市。現在,很多活動都取消了,收入減半,“幸好還沒有孩子要撫養。”現在片區內憑通行條出行,辦公室里養了4只貓,他在擔憂萬一管得嚴,怎么把貓運出去。

●凌晨沙園市場一角。攝影/Pingolau 劉
人群快要散去的時候,豬肉攤主吳天明才想起自己要買點青菜,發現菜價也翻倍地漲,買了幾斤生菜就花了五六十塊。他的豬肉還沒到,一直到早上七點。這是整個市場最晚的一批貨,但并不妨礙當天的生意,早起的老年顧客涌進來,也是一個小時就賣完了。
這時,熟客過來,要昨晚在微信上預訂的肉,生氣地質問他:“你怎么這樣子啊?都提前叫了你留的。”他趕緊好聲好氣地道歉,“不好意思,我忘了。”瘋狂搶購潮過去,面對熟客他也不敢漲價,還是按正常價賣。吳天明收拾好攤子已是10點,回到家沉沉睡去。
他租的房子就在市場里,攤位1.6米長,不到兩平方,他和妻子成天守著。每天5點起床,出攤,晚上收攤,收拾好已經9點,要睡覺了,只有春節時休息五六天。他沒去過廣州什么景點,“實力不允許”——三個孩子,大兒子在老家讀初中,兩個小的在廣州讀私立小學,一個人每學期學費要七千多元。房租一個月也要兩千元,還不包括水電費。
菜市場流動性大,只要城里有病例就會受影響,9月份關過一周,不久前也歇業了兩天。“頂不住也要頂”,吳天明說,回老家只能種地。兩個孩子已經停課三周了,之前夫妻倆做生意要帶上手機,出租屋里沒有多余的手機讓孩子上網課。這幾天有了,但孩子一拿到就玩游戲,“唉,管不了”,吳天明連連嘆氣。
Sandy女士睡到下午才起來。晚上六點多,她為家人做了豐盛的一餐,魚腩煎得金黃再燜一下,燜出滿滿的膠質;豬肉漲價了,但是生活沒有肉是不行的,做一盤豉汁蒸排骨;前兩天買了只靚雞,她把肥膏和肥的皮切出來榨油,雞油用來炒菜花,口感清爽。“即使是最簡單的食材,也要做得有滋有味,這便是廣州人的美食哲學。”
一個從市場搶購回來的年輕女孩開始害怕,擔心萬一這里有人“陽”了怎么辦?她告訴了一些路人還有貨“趕緊去搶”,轉頭又想,自己是不是制造了恐慌?
去了三次市場的貴哥回到宿舍,和舍友在上下床的狹小空間里無事可干,沒有短視頻可拍了,他吃完飯又繼續上床躺著,刷刷手機或是睡一覺。其他博主在菜市場拍的視頻傳到網上,配上爵士樂火了,網友評論說像李安的風格,“你是懂情調的,就差一杯Dry Martine了”。
(據講述者意愿,文中除韓冠聲外,均為化名。頭圖與封面圖均為Pingolau 劉的攝影作品,特此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