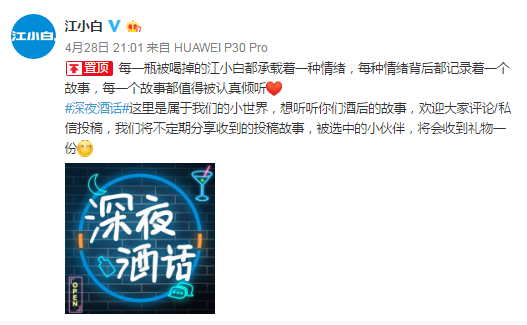年輕人不愛喝白酒,早就不是什么新話題,但搶購茅臺和購買白酒股票的人群中,又不乏年輕人的身影。為了爭取這塊消費市場,近兩年來,知名白酒品牌也使出渾身解數,紛紛為“年輕化”按下加速鍵,這一次,茅臺們還能如愿以償嗎?

文: 阿瞞
來源:新周刊(ID:new-weekly)
最直觀的是售價,以茅臺為例,盡管“原價茅臺”仍然是市面上的稀缺品,但是相比于巔峰時期,炒作空間已然萎縮不少。當然還有一瀉千里的股價,僅僅10月一個月份,滬深兩市20家白酒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蒸發了1萬多億。
仍然以茅臺為例,曾被《華爾街日報》稱為全球投資者排隊都想嘗一口的“煤油味兒”股王,跌到了兩年來的低谷。
遙想2020年,茅臺股價連創新高,總市值不僅超越了貴州省上一年的GDP總量,也把百年巨頭可口可樂甩在身后。彈指間三年過去,一切好像又回到最初的起點,只是不知道中途有多少人套現離場,有多少人高位接盤。作為資本市場的寵兒、中國餐桌的頂流、社交場合的剛需品,白酒周遭從來不缺少爭議。隨著時光變遷,一些爭議的答案逐漸明晰,比如白酒股價會不會一直漲下去,茅臺是不是穩賺不賠,而還有一些由來已久的議論,被推到了眼前。比如,95后、00后不愛喝白酒,白酒以后要賣給誰?喝白酒的人是不是真的變少了?也許可以從銷量和產量上尋找端倪。今年中秋以來,白酒庫存嚴重、行銷不暢的新聞就屢屢出現,往年,從中秋、國慶再到元旦、春節,是中國人團聚、宴請、招待、婚禮的集中期,也是白酒銷售的黃金月份,但今年,“旺季不旺”是普遍的感受。 天下第一瓶。/圖蟲創意如果僅僅把這種銷售不順歸因于短期疫情影響,那么把時間線再拉長,也許能看到更加明顯的趨勢。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白酒的產量在2016年到達峰值,隨后便一路下降,到2021年,規模以上酒企產酒量剛剛超過700萬千升,幾乎只有峰值時的一半。如果將白酒視作佐餐飲品,那么市面上比它價格更便宜、口味更好接受、對工作影響更小的飲品,比比皆是;如果將白酒當做談判應酬時的必需品,那么它自然也扮演了經濟晴雨表的角色;如果將白酒視為婚宴、家宴的“面子工程”,那么逐漸走低的結婚率和原子化的家庭規模,也讓那種需要白酒點綴的宴會越發稀有。我們見到白酒的場合越來越少了,背后是白酒的一系列社會功能在逐漸瓦解。這種情況,也許促成了白酒市場的進一步集中,盡管行業進入下行通道,但處在頭部的一批酒企,仍然是中國最賺錢的一批企業。根據前三季度財報,20家上市酒企的總營收接近1700億,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16%,凈利潤更是合計超過千億大關,比去年大漲21%。打頭的茅臺用9個月時間,達成871億營收,444億利潤,“茅臺日賺1.6億”的詞條沖上熱搜。在這個很多人感到艱難的時刻,一天一個小目標的標題,的確具有沖擊力。令人羨慕的不僅是龐大的營收規模,還有極高的賺錢效率。前不久,曾有媒體盤點過一份《2022中國食品飲料百強榜》,評選出國內前100名的本土食品飲料企業,其中排在第一、二名的是伊利和茅臺,分別代表白酒和乳品兩大品類,進入“營收千億”行列。根據公開信息,伊利2021年的營收達1105億,貴州茅臺則是1094億,相差不多。但再對比利潤,茅臺賺了524億,伊利賺了87億,相差懸殊,白酒行業利潤率之高可見一斑。一邊是根基松動的市場,一邊是逐年積累的巨大收益,目光放長遠看,年輕人是未來白酒企業必須攻下的一塊陣地。如果說江小白是找準了被行業忽略的年輕消費市場、從空白地帶闖出來的新銳,那么,后知后覺的傳統酒企們,也紛紛開始調動雄厚的資源,瞄準年輕人。只不過從目前來看,這種“聯動”更多的還只是一種單相思。樂觀者覺得,這恰是中國人擺脫酒桌文化乃至人情社會的寫照,悲觀者表示,隨著年輕人成長為社會消費的主力軍,白酒神話會進一步破滅。也有看破紅塵者做出預言,年輕人不愛喝酒,只是閱歷未到,總有他們融入酒桌、習慣推杯換盞的一天。今天的年輕人成了明天的中年人,他們還愛喝酒嗎?/ 圖蟲創意對于這個問題,茅臺集團原董事長季克良曾做過正面回答。在兩年前的一檔訪談節目上,面對“年輕人不喝茅臺”的問題,時年80歲的季老精神矍鑠,坐在沙發上神情輕松,從容回答:“說年輕人不愛喝茅臺酒,我說還沒到時候。二十來歲,小孩子還不懂事,不曉得喝好酒呢。”接著季老談起自己的喝酒感悟,稱自己“喝過的茅臺酒都快兩噸了”,每天早晨品一次酒,半兩到一兩,中午“喝個二兩”,晚上喝三兩。這段聽上去有點傲慢的回應,和早中晚飯依次遞進的飲酒習慣,注定只會引起年輕人的反感。愛不愛喝先不談,光是這一天半斤多的茅臺酒,折合成售價,就足以讓年輕人郁悶了。當然,季克良也有過“希望讓工薪階層喝得起茅臺,讓茅臺走進千家萬戶”的發言,但對于互聯網上的內容,人們記住的總是最扎心的那部分。另一位茅臺集團原董事長李保芳,也曾在2018年談到過,年輕人不喝茅臺將來會變成“大麻煩”。但一位商業巨鱷當時安慰他:“不用擔心,我小時候也特討厭茅臺,但是等我有了人生閱歷、吃了很多苦頭以后,我覺得茅臺還是很有意思的。”但迅速變化的市場,未必就能讓酒業巨頭們高枕無憂,說歸說,做歸做,近兩年來,知名白酒紛紛為“年輕化”按下加速鍵。然而,這些標榜著年輕化的產品,在真正的年輕人看來,卻總有些別扭。比如汾酒旗下的“鬧他小酒”,用“鬧他”這句山西方言命名,大概意思是天不怕地不怕,迎難而上;瀘州老窖與雪糕的聯名產品叫“斷片”,大概是忘記煩惱的含義;紅星二鍋頭“將所有一言難盡一飲而盡”的廣告語,也是類似的思路。這種看似創新的品牌打法,實則和白酒曾經俘獲中年人的邏輯如出一轍——讓中年人盡情感慨豪邁,讓年輕人盡情張揚個性。我們可以回憶一下那些經典的白酒廣告,從“喝出男人味”的老白干,到“往事越千年”的白云邊,從“悠悠歲月”的沱牌曲酒,到“難得糊涂”的小糊涂仙,基本是酒桌常見話題的復刻。而號稱更懂年輕人的江小白,打出的是“吃著火鍋唱著歌,喝著小白劃著拳,我是文藝小青年”,幾乎要把“我懂你”刻在瓶身上。
天下第一瓶。/圖蟲創意如果僅僅把這種銷售不順歸因于短期疫情影響,那么把時間線再拉長,也許能看到更加明顯的趨勢。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白酒的產量在2016年到達峰值,隨后便一路下降,到2021年,規模以上酒企產酒量剛剛超過700萬千升,幾乎只有峰值時的一半。如果將白酒視作佐餐飲品,那么市面上比它價格更便宜、口味更好接受、對工作影響更小的飲品,比比皆是;如果將白酒當做談判應酬時的必需品,那么它自然也扮演了經濟晴雨表的角色;如果將白酒視為婚宴、家宴的“面子工程”,那么逐漸走低的結婚率和原子化的家庭規模,也讓那種需要白酒點綴的宴會越發稀有。我們見到白酒的場合越來越少了,背后是白酒的一系列社會功能在逐漸瓦解。這種情況,也許促成了白酒市場的進一步集中,盡管行業進入下行通道,但處在頭部的一批酒企,仍然是中國最賺錢的一批企業。根據前三季度財報,20家上市酒企的總營收接近1700億,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16%,凈利潤更是合計超過千億大關,比去年大漲21%。打頭的茅臺用9個月時間,達成871億營收,444億利潤,“茅臺日賺1.6億”的詞條沖上熱搜。在這個很多人感到艱難的時刻,一天一個小目標的標題,的確具有沖擊力。令人羨慕的不僅是龐大的營收規模,還有極高的賺錢效率。前不久,曾有媒體盤點過一份《2022中國食品飲料百強榜》,評選出國內前100名的本土食品飲料企業,其中排在第一、二名的是伊利和茅臺,分別代表白酒和乳品兩大品類,進入“營收千億”行列。根據公開信息,伊利2021年的營收達1105億,貴州茅臺則是1094億,相差不多。但再對比利潤,茅臺賺了524億,伊利賺了87億,相差懸殊,白酒行業利潤率之高可見一斑。一邊是根基松動的市場,一邊是逐年積累的巨大收益,目光放長遠看,年輕人是未來白酒企業必須攻下的一塊陣地。如果說江小白是找準了被行業忽略的年輕消費市場、從空白地帶闖出來的新銳,那么,后知后覺的傳統酒企們,也紛紛開始調動雄厚的資源,瞄準年輕人。只不過從目前來看,這種“聯動”更多的還只是一種單相思。樂觀者覺得,這恰是中國人擺脫酒桌文化乃至人情社會的寫照,悲觀者表示,隨著年輕人成長為社會消費的主力軍,白酒神話會進一步破滅。也有看破紅塵者做出預言,年輕人不愛喝酒,只是閱歷未到,總有他們融入酒桌、習慣推杯換盞的一天。今天的年輕人成了明天的中年人,他們還愛喝酒嗎?/ 圖蟲創意對于這個問題,茅臺集團原董事長季克良曾做過正面回答。在兩年前的一檔訪談節目上,面對“年輕人不喝茅臺”的問題,時年80歲的季老精神矍鑠,坐在沙發上神情輕松,從容回答:“說年輕人不愛喝茅臺酒,我說還沒到時候。二十來歲,小孩子還不懂事,不曉得喝好酒呢。”接著季老談起自己的喝酒感悟,稱自己“喝過的茅臺酒都快兩噸了”,每天早晨品一次酒,半兩到一兩,中午“喝個二兩”,晚上喝三兩。這段聽上去有點傲慢的回應,和早中晚飯依次遞進的飲酒習慣,注定只會引起年輕人的反感。愛不愛喝先不談,光是這一天半斤多的茅臺酒,折合成售價,就足以讓年輕人郁悶了。當然,季克良也有過“希望讓工薪階層喝得起茅臺,讓茅臺走進千家萬戶”的發言,但對于互聯網上的內容,人們記住的總是最扎心的那部分。另一位茅臺集團原董事長李保芳,也曾在2018年談到過,年輕人不喝茅臺將來會變成“大麻煩”。但一位商業巨鱷當時安慰他:“不用擔心,我小時候也特討厭茅臺,但是等我有了人生閱歷、吃了很多苦頭以后,我覺得茅臺還是很有意思的。”但迅速變化的市場,未必就能讓酒業巨頭們高枕無憂,說歸說,做歸做,近兩年來,知名白酒紛紛為“年輕化”按下加速鍵。然而,這些標榜著年輕化的產品,在真正的年輕人看來,卻總有些別扭。比如汾酒旗下的“鬧他小酒”,用“鬧他”這句山西方言命名,大概意思是天不怕地不怕,迎難而上;瀘州老窖與雪糕的聯名產品叫“斷片”,大概是忘記煩惱的含義;紅星二鍋頭“將所有一言難盡一飲而盡”的廣告語,也是類似的思路。這種看似創新的品牌打法,實則和白酒曾經俘獲中年人的邏輯如出一轍——讓中年人盡情感慨豪邁,讓年輕人盡情張揚個性。我們可以回憶一下那些經典的白酒廣告,從“喝出男人味”的老白干,到“往事越千年”的白云邊,從“悠悠歲月”的沱牌曲酒,到“難得糊涂”的小糊涂仙,基本是酒桌常見話題的復刻。而號稱更懂年輕人的江小白,打出的是“吃著火鍋唱著歌,喝著小白劃著拳,我是文藝小青年”,幾乎要把“我懂你”刻在瓶身上。
從小到大,總有幾個白酒廣告讓你忘不了。/ 圖蟲創意但這種 “迎合”顯然是淺顯而生硬的,真正的年輕人看了也大概率是一笑了之。直到今年,帶頭大哥茅臺出手,推出聯名產品茅臺冰淇淋,一度刷屏,終于有了點接近年輕人的意味,只不過原價60塊的冰淇淋,最高被炒上過3000塊,成了“雪糕刺客之王”。對于其他品牌蹭熱度的“茅臺+”行為,比如茅臺咖啡、茅臺炒酸奶等等,茅臺官方也沒有明確拒絕,幾輪出圈后,茅臺這一白酒符號完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年輕化”更新。但不管是酒企還是年輕人,心里都明白,白酒當下真正的“基本盤”還是酒桌上的中年人。年輕人不過是嘗試爭取的未來,中年人才代表寸土必爭的現在,比如紅星二鍋頭最近請來了明星張涵予代言,廣告語依舊是“幾輩人都喝它”的懷舊風,目標受眾是誰,不言而喻。從這個角度來說,從過去、現在直到未來,年輕人的身份始終都是白酒主流敘事話語里的邊緣人,是中國酒桌上的隱身者。有報告顯示,中國30歲以下消費者的酒類消費中,白酒僅占不到一成。根據騰訊營銷洞察在今年上半年發布的《2021白酒行業數字營銷洞察白皮書》,年輕人購買白酒主要用于社交、投資、送禮,日常飲用很少。但搶茅臺和購買白酒股票的人群中,又不乏年輕人的身影。今年3月,茅臺推出售價399元的100ml飛天茅臺,就像是一次對年輕人的適配。但在投資屬性逐漸退去的當下,年輕人對于白酒的恐慌和疏離并沒有改變。這種辛辣的飲品幾乎是酒桌文化的代名詞,酒桌上的觥籌交錯,是前浪給后浪設置的考驗,也是前浪們辨認彼此的方式。最讓人厭惡的勸酒,背后隱含的權力邏輯和服從測試,是年輕人最不愿意回憶的社會場景。要么緘默不語,要么勉強喝下,要么調整心態積極融入,喝與不喝間,“屠龍少年變惡龍”的橋段反復上演。正如小說《滄浪之水》中所寫:“自己以前從不喝酒,現在成了個酒仙,喝酒是跟領導拉近感情距離的一條重要途徑。”局中人對于白酒自然是享受的,但年輕人卻往往感到無措甚至難堪。年輕人疏遠白酒,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一些堅固的社會規訓的疏遠。但這種疏遠能不能真正保持下去,而這些規訓會不會換一種更加溫和的方式出現,則關乎“拒絕的自由”究竟能保持多久。還記得去年火過一輪的熱紅酒嗎?今年已經脫離地攤、飛入便利店。散裝的熱紅酒變成了瓶裝,方便、廉價、安心,幾塊錢就可以買上一罐,拍幾張文藝的照片,然后飲盡。雖然消費主義是一個幾乎被用濫的詞,但事實證明,它總是能針對年輕人的偏好,演化出更加新穎溫和的“勸酒”方式。告別傳統酒桌的劍拔弩張,世界仍有許許多多的辦法,讓年輕人在誤以為的自由中,把一些產品和道理一飲而盡。


 天下第一瓶。/圖蟲創意
天下第一瓶。/圖蟲創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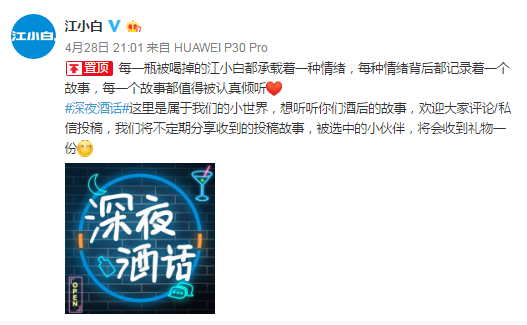





 天下第一瓶。/圖蟲創意
天下第一瓶。/圖蟲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