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法國畫家讓·弗朗索瓦·米勒有一幅名畫《土豆收獲者》。昏暗的風景線之下,人們在將土豆裝袋。一袋袋裝滿的土豆放在旁邊,顯示這又是一次豐收。畫家的畫讓我們知道,在19世紀,土豆已經成為歐洲農村的重要作物。彼時,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物種遷移完成了本土化,為當地人所普遍接受。

讓·弗朗索瓦·米勒《土豆收獲者》
如今土豆已是我們餐桌上的常客,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土豆是怎樣從新大陸漂移到舊大陸,從而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命運的呢?
南美大陸,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稱之為“憂郁的熱帶”,在幾千年的生命時光里,印第安人在此孕育了輝煌的文明,也馴化了許多重要的作物,土豆便是其中之一。

弗朗西斯科·皮薩羅
1533年,西班牙文盲冒險家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征服了印加帝國,于是也發現了當地人特有的食物——土豆。在滿載著掠奪來的金銀珠寶的貨船上,土豆開始了在歐亞大陸的最初冒險。
坊間一直流傳一種說法,土豆拯救了整個世界。這一說法究竟有多少根據呢?
許多人可能不信,但是導演陸川卻相信,因為他親眼見證了土豆的奇跡。
01
土豆拯救世界?
且不說土豆有沒有拯救世界,土豆的確拯救了“馬特·達蒙”——在科幻電影《火星救援》中,馬特·達蒙飾演的宇航員滯留在火星,靠著對陽光、水分、養分的精準把握,成功種出了土豆,最終延續了生命。

《火星救援》劇照
科學照片上可以看到,火星是真正的不毛之地,那里沒有氧氣和水分,什么作物都不能生長,但人們還是還是愿意接受能在上面種出土豆的設定——因為土豆實在是太能適應極端環境了。只有你想不到,似乎沒有土豆不能生長的地方。甚至沙漠!
讓我們跟隨導演陸川的鏡頭,去看土豆如何在沙漠中扭轉乾坤吧。鏡頭隨著無人機飛向天空,俯瞰大地,在無垠的荒漠之中,一片片綠色的圓圈出現在我們眼前。那就是土豆在沙漠中所組成的綠色長城。

庫布齊沙漠農場俯瞰
綠色長城的背后,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課題。不僅要先對堿性土地進行改良。沙丘上建大型噴灌,還要在噴灌圈外栽種樹木,防風固沙。種植時,還需要選取優質的馬鈴薯種子,悉心栽培,天氣和土壤等影響栽培的因素在這里表現得更為極端。視頻中,種土豆的主人公叫陳喜良,是現實中沙漠中種植者的一員。他說:“4年的種植,7個月的堅守。”短短的一句話,背后是汗水和歲月沉甸甸的分量。

種植者陳喜良在農場勞作
“時間是山河的倔強,土地是人的夢。”喜歡詩歌的陳喜良曾經這樣寫道,在時間的長河里,人在土地上造出了自己的夢。從這句詩里,陸川看到了沙漠中種土豆者的堅守,感受到了時間在陳喜良身上的印記,也強烈地感受到了土地對于這些堅守在庫布齊英雄們心中的分量。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綠色長城也是在不斷與狂風、沙暴做斗爭中一點點生長出來的。陸川很喜歡這樣的異域場景,對他來說,拍攝就像是一場旅行,而這場旅行最讓他感動的是真實。在當地拍攝用的大多是當地人,勞動者們擦土豆的動作尤其令陸川印象深刻,他們會用手掌根部珍重地去抹一下,“農場工人拿土豆的方式和他們用手抹去土豆上的沙粒的方式,特別像是撫摸自己的孩子。”


農民用手抹去土豆上的沙粒
然而,飽含著勞動者心意的土豆,想要被人們吃進口中,還要經歷另一層冒險。
當年,能夠適應極端環境的土豆,從美洲大陸旅行到歐洲大陸之后并沒有得到重視,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人們并不吃它,還對它進行污名化。直到有一天,饑荒發生了。當人們不得不考慮用什么作物來抵御饑荒的時候,一向被人輕視和污蔑的土豆被推上了前臺。

土豆“正名”第一步
1770年代,一場因寒流引發的饑荒在法國蔓延,法國科學院就“災年減饑食糧”的主題舉行征文,一位藥劑師推薦了土豆,這篇文章披荊斬棘最終獲獎,這是土豆在歐洲正名的第一步。
不過“成也土豆,敗也土豆”,人們一旦對土豆產生依賴,彼此的命運就牽連在一起了。土豆不能生病,更不能減產。從這個角度來說,土豆確實拯救了世界,它與其他量產作物一起為世界人口的繁衍提供了“后勤保障”。可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土豆只是特定階層的食物,這又是為什么呢?
02
土豆征服人類味蕾
飲食人類學家有一個基本結論:食物是有“階層”之分的,不同的人群會青睞不同的食材。簡單說來就是:你吃什么,你就是誰。土豆一開始只是勞動者的食物。這一點我們從米勒和梵高的畫里就能看出來,在那些風格偏暗的畫作之上,土豆扮演了勞動者的“面包”角色。梵高寫道:“吃土豆的人用他們同一雙在土地上工作的手從盤子里抓起土豆。”而當時,那些不需要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對土豆則不屑一顧,有一個原因說來可笑,他們覺得土豆長得太丑了。
在推廣土豆這件事上,歐洲知識階層沒少費力氣。在西班牙,有人將土豆獻給教皇,在法國,有人把土豆花送給王后,在英國,皇家農學會積極號召人們種植土豆。經過一兩個世紀的普及,土豆已經成為各個階層人士的食物,只是在食用的方法上稍有不同。勞動者還是習慣于整體煮熟了吃,而更高階層的人士則更愿意將土豆經過一道烹飪的手續。

帕蒙蒂埃向國王和皇后展示土豆植物
薯片最初便是土豆的一種高級吃法,在土豆普及的過程中,薯片可謂功不可沒。那你知道,薯片誕生于一次抱怨嗎?這更像是一個戲說,而不像是真事。
喬治·加林在紐約州北部長大,1850年,他受雇于一家為曼哈頓富裕家庭提供服務的高級餐廳。一位挑剔的顧客抱怨薯條太厚。由于對這位顧客非常反感,喬治準備“報復”他一下,于是他把一批土豆切成紙一般薄,繼而油炸成酥脆,并用大量的鹽調味。然而報復不成,顧客卻很喜歡這種土豆新吃法。很快,加林和這家餐廳就因為他們的特殊“薩拉托加薯片”而聞名。

喬治·加林的Lake House餐館
盡管對于薯片究竟是誰發明的還有爭議。但歷史的官司歸于歷史,人們對薯片的熱愛卻從其一出現就一發不可收拾,富人可以在高級餐廳享用,其他人在家中便可完成簡單烹制。不過薯片真正引領人類消除飲食的階層差異,主要原因是一個薯片工業體系的崛起。薯片的大規模生產,大范圍消費,這些都定義了薯片本身,也規范了食客們對薯片的期許與想象。
那你知道一片現代工業體系中的薯片是如何誕生的嗎?這也是陸川所好奇的,一個蒙太奇手法,庫布齊農場的風沙、緊張與孤絕等場景得以轉移,薯片工廠的故事以一車長途跋涉的土豆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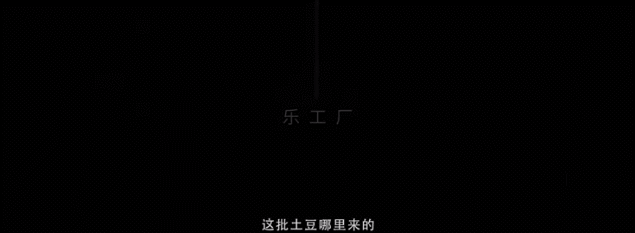

土豆由庫布齊農場運送到薯片工廠
影片中,在濱江之城武漢寬敞明亮的廠房里,50噸庫布齊土豆兄弟們經過4年的培育,在這里將進行一場身體的分離式,在豎琴演奏的巴赫音樂背景下,陸川鏡頭下的薯片工廠快樂而有節奏。為了更好地拍攝,陸川主要以Macro微距鏡頭為主,以更好地用特別表現機器生產的工業美感與薯片的金黃薄脆。拍攝時,陸川帶著攝影機走遍了生產線上幾乎每一個流程和細節。
面對整個工業化流程,陸川贊嘆不已。工業化不再是冷冰冰的科技感和大機器,而是有一種匠心蘊含其中,那種精準和智能化是陸川所想要表達的。他說:“工廠精密得讓你嘆為觀止,土豆進去之后,先進行清洗,控制濕度溫度,甚至每一片厚度都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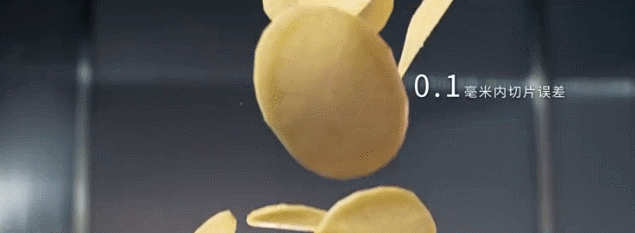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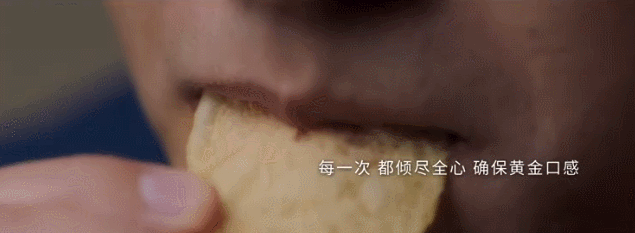
工業化對應的精細化,體現在極致而細微的數據上
為了保證每一片薯片都有相同的口感和品質,切片誤差控制在0.1毫米內,加工薯片的時間也精確到秒以保證最恰當的香脆,每一批次的薯片都需要與黃金表樣進行對比。
金黃薄脆的背后,是工人們對于自己工作的執著和一絲不茍。當身處于冷庫之中,陸川和薯片工廠的冷庫主管瞿明面對面,瞿明在手電筒燈光下用手拿起土豆翻看的動作尤其讓動容。在瞿明看著土豆的那種嚴謹和執著的眼神中,土豆像是有生命的、有溫度的,即便是在冷庫里,面對堆積如山的土豆,他們像是在一起呼吸。
拍攝時,語言動作的設計都顯得冗余,陸川只是用鏡頭自然捕捉到了他的真實狀態,便能讓觀眾感受到瞿明說的“把東西做到多好,永遠是自己和自己的較勁兒”這句話的分量。“我們在吃薯片的時候并不會關注每一片的薄厚,但其實他們在背后做了很多工作。”

薯片工廠的冷庫主管瞿明
工業化帶來薯片的進一步普及,薯片則不負眾望打破了食物的階層界限,對大眾社會的到來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你可能會說,薯片有那么大能耐?你不信——盡管在提出質疑的時候,你正在吃著薯片。你應該相信,因為薯片背后是一個誰都無法抗拒的法則。
03
土豆拯救的世界
薯片令其快樂
薯片的法則很簡單,那就是快樂。瑞士心理學家海因里希·貝格爾可謂深諳薯片在人心理上的功用,他在《解夢心理學》一書中寫道:“夢見薯片,通常象征快樂的生活和溫暖的家庭。”但是他又說了,要是夢見自己狂吃薯片,那可能是因為心中有愿望沒有實現,內心略帶失落。不過歸根結底,心理學家的意思都是,薯片終究是快樂源泉,快樂時想吃它,不快樂時更需要它給自己帶來快樂。
薯片的快樂法遵循的是分享的藝術。薯片在工廠成形裝袋之后,還要經過一段漫長的跋涉才能抵達你我中間。旅途的短暫停靠點是倉庫,曙光乍現之際,配送員的一天從這里出發。對于薯片來說,這才是一段刺激旅程的真正開始,它們將要面對最終的檢驗——食客們那挑剔的舌尖。


樂事配送員將薯片送到無數小商店
如果薯片是快樂法則的扮演者,那么配送員便是快樂的搬運工,陸川的鏡頭跟隨這位快樂散布者的步伐,在上海這座城市里穿梭往來。通過她的眼睛,陸川看到了這座城市最日常的一面,他關注到上海無數小商店,那是樂事薯片走向食客的最后一站。東方明珠塔在配送員的后視鏡中后退,社區將迎來最新出品的樂事薯片,人們在各自的生活里經受著喜怒哀樂,而配送員像是路過的天使一般凝視,卻又走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是愛人之間的久別重逢,是人生職場的不盡如意,是社區的一場象棋大賽,是商店半夜的幽微燈火。


薯片為人們帶去分享的快樂
在陸川的鏡頭下,樂事薯片的冒險旅程中人間百態盡顯。最終,樂事薯片停留在一排排的架子上,等待著迎接一個個真誠而燦爛的微笑。配送員的一天也在這時候進入尾聲,太陽早已歸歇,大地上的華燈依然演唱著不夜的歡歌,為夜歸人送去些許溫暖。微笑最終會迎來微笑,每一份善意都有回響。
1993年,百事公司引進樂事薯片進入中國市場。27年來,百事在中國的食品業務已發展了18個農場和7家工廠,庫布齊沙漠農場和武漢工廠是其中的代表。陸川說:“薯片這種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零食,其實背后有著非常壯觀的一個產業鏈在支撐,而產業鏈的每一個細節都決定了薯片品質的好壞。”
通過大量有關樂事薯片的采訪和調研,他很為這種“用心”精神所感動,每一袋薯片背后都承載著太多人的堅守和匠心精神,“用心”體現在每一個瞬間,從沙漠中的種植者,到工廠的技術員,再到將薯片送達顧客手上的配送員,他們傾心澆灌著這一棵快樂之樹,讓微笑之花開在每一個食客臉上。
點擊視頻,觀看土豆成長為薯片的快樂冒險
樂事配送員說:“我們把快樂交到你的手上,也從你手上到更多人手上。”樂事薯片的旅程,正是一次微笑的旅程,也是一次分享微笑的旅程。而這一切的開始都和土豆的世界旅程有關,土豆的旅行終點何在,我們還不知道,但科學家已經做出預測,在未來,土豆將繼續拯救世界。
那么薯片呢?也會繼續讓人微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