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秋,青島,一年一度的全國肉業展,場館外,有一個名為“瑯琊閣”的海鮮食坊,吸引了大量參展的客商,似乎都想去找一找登臨瑯琊榜的感覺。
然而“瑯琊”一詞的由來,比架空的瑯琊榜要久遠得多,這是春秋時期,青島一帶的郡縣名,著名的千年士族世家瑯琊王氏,便出于此間。
但店名的典故并不重要,展會期間,圈內人招呼著平時在天南海北的新朋舊友,來這里吹著海風低斟淺酌,酒至半酣處,還是能生出江左梅郎乘舟江湖的豪氣的。
01
2020年,中國肉品業的瑯琊榜上,雙匯是無可置疑的第一。
展會前夕,總市值在高歌猛進的豬市與股市上剛過兩千億,完成了現任總裁前年上任時官宣的第一個目標,達到了行業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據說新征程的任務,是尋找行業的新方向——雙匯拔劍四顧,已無對手。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現在意氣風發的雙匯,似乎早已完全從近十年前的那場風波中走出,克服了傳統企業滯漲的瓶頸,也似乎成為肉類行業的“黃埔軍校”。
同一時期網上與其它友商關于“搶人大戰”的口水戰,一點都不影響各個時期的雙匯人,穿著不同廠家的制服重逢在展館里,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雙匯亮眼的成績,固然離不開主政者極強的經營能力,全體員工常態并不限于996的努力工作,以及愈演愈烈的豬周期的全力加持,而對手缺席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十年前,肉類行業的老大,是金陵的雨潤。
02
與1984年開始改制的雙匯相比,雨潤更年輕一些,創始人祝義財是著名的92派。
1992年是一個很奇妙的年份,隨著一位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風起云涌的改革開放大時代正式到來。
這一年,安徽人祝義財放棄公務員身份,下海挖出第一桶金后,初創合肥華潤(雨潤的前身)。

同一年,鄰省的秦英林也不約而同的放棄公職,回家開始養起22頭豬。
而現在許多著名的肉類企業也都誕生在那一年之后,例如,成立于1993年的眾品,成立于1994年的金鑼。
相信那個時間點,豬周期還未形成氣候,正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剛剛吃飽的人民群眾消費能力進一步升級,養豬殺豬前景可期。
2010年,已經擁有冷鮮、冷凍豬肉與常溫、低溫肉制品生產線的雨潤,收入同比上升55%至215億元,凈利增長56%至27億元。祝義財被授予“功勛企業家”稱號。
那時候,雨潤的發展順風順水,如日中天。
03
再上一個十年,雙匯的火腿腸剛悄悄取代了鄰居春都,成為國人心中的火腿腸第一品牌,并從國外引進冷鮮肉生產線。
在當時一把刀一盆熱水就殺豬的中國,斥巨資生產冷鮮肉的舉措需要極大勇氣。
然而,萬隆堅定地認為,那才是中國屠宰業的方向,力排眾議上馬了這個新項目。

2010年時,雙匯已經成立了鮮凍品事業部,這個新的部門為火腿腸生產提供配套的同時,還向市場銷售冷鮮肉。
當時的國內鮮肉市場充滿了地方保護,冷鮮肉的拓展相當艱難,即使如此,仍然以品質與價格的優勢,占有了雙匯總營收的39%。
那時,朱龍虎與馬相杰分任鮮凍品事業部的總經理與生產副總。
兩個30多歲的年輕人應該沒有想到,十年之后,他們已經分別是兩大肉企的總裁。而雙匯的鮮凍品事業部已強勢超過肉制品事業部,占據了61%的營收比例。
04
2009至2011年,堪稱是雨潤發展歷史上的巔峰時期。
2009年,首長在雨潤總部調研時,深情寄語:“我相信,中國這么大,農業涉及的面這么廣,我們應該有一個發達的食品工業。希望你們兢兢業業,一絲不茍”。
2010年底,雨潤以2.56億元,一舉拿下“2011年央視廣告第一標”,包攬央視《新聞聯播》后首條廣告位。
到2012年,其首破千億,集團營業收入1061億元,同比增長17%。
這一年,祝義財開始徹底不管食品板塊,將食品板塊交給他看中的職業經理人,轉身投向地產等多元化產業的構建。
然而,從2012至2020年,縱使祝義財幾近缺席肉食的這8年,也無人突破他的高光時刻,包括現在的老大雙匯。
但,雄才偉略的祝義財,在走上地產的吸金快車道,卻也失去了繼續稱霸肉業的機會。
相對祝義財,比他資歷更深的兩個行業大鱷則更富傳奇。
新希望的劉永好,在八十年代就成立了飼料公司;藥學專業出身的明金星,早在八十年代就吸金數百萬,并于九十年代初投資了金鑼。
明金星頗具隱士風范,明明是大股東,絕大多數事務卻都由大學校友兼合作伙伴周連奎出面,他自己長年呆在香港,一年去企業的次數也就三五次。

2010年,劉永好將新希望交給了女兒劉暢。當爹的愛女心切,扶上馬后送了一程又一程。從陳春花,再到80后“地產新貴”張明貴,劉暢任新希望六和董事長的7年里,已經更換了四任總裁。

而金鑼,這十年來,從伊利空降而來的職業經理人郭維世,卻在總裁任上穩如泰山,公司與媒體的宣傳中基本見不到明金星周連奎兩位老板的蹤影。不可忽視的是,在食品這個中國傳統的業態中,家族傳承式的接力棒,遠多于西方企業的職業經理人模式。

05
秦英林作為92派的代表,近兩年迎來了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92派人士的共性是,文化程度高兼具有下海的膽識,例如泰康人壽的陳東升與地產三君子。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投身養豬行業的老板,則大多是北方農村貧窮家庭出身,拼搏成了小地方的大企業,漯河的萬隆、長葛的朱獻福莫不如是。
河南農大畢業的南陽內鄉人秦英林,兼而有之。
這個在高中時就關注養豬,并因此報考農校的河南首富,還是個被養豬事業耽誤的文學青年。

2010年時秦英林親自寫出了著名的《拜豬文》。而在牧原每年的大型活動上,總有一個特別環節,秦英林與員工們一起,激情朗誦自己在2008年的某個凌晨創作的《胡楊贊》,有內部人士認為該詩歌是秦的自畫像——“不屈不撓,勇敢堅強,平和樂觀,屹立不倒。”
對企業文化的深情關注固然是極好的,可是文藝色彩的用力過猛,總讓外人覺得偏理想主義。
2020年,牧原正式進軍屠宰業的前夕,準供應商們被建議交納“業務員廉潔保證金”,這種清奇脫俗的關于押金的說法,讓未經相關文化洗腦的目標客戶,望著對面牧原業務員的認真臉,一臉懵逼。
然而首富畢竟是首富。雖然養豬業沒有屠宰企業那么吸引眼球,但是近十年來每次豬周期的高位時期,都是養豬企業的主場大秀。
上上次,牧原、雛鷹、溫氏三國爭霸;上一次,牧原、雛鷹上演喋血雙雄;這一次,連吹牛都改成吹豬的史上最烈豬周期中,牧原已經成為武林至尊。
有一則關于首富的段子是這樣的:“想一夜暴富嗎?你只要去養二十頭豬……”可是近三十年下來,養豬已經是王健林聽了嫌貴、阿里網易爭投的高大上的重投入行業,人不如豬早已成為常態,牧原的豬不僅住的是高層建筑,據說室內潔凈標準堪比醫院的ICU病房。養豬從房前屋后的小農經濟,越來越向高集中度、高科技化發展,隨著環保政策的日趨嚴厲,個人養豬走上致富路已成為不可復制的神話。
06
說起殺豬賣肉,國內最具有話題性的人物,卻不是上述任何一位老板,而是一個書生——畢業于北大的陜西人陸步軒。
2003年,一則名為《北大才子長安街頭賣肉》的報道將這個60后推上“熱搜榜”,陸步軒幾乎抬不起頭來。即使當時的行業巨頭,個人身家早已過百億,殺豬賣肉不屬于高尚職業,仍是國人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
當時的陸步軒不知道,17年后,他的校友李雪琴在脫口秀節目里,淡定地喊出:“北大怎么了?念了北大就不能當一個low逼了嗎?念了北大就不能當一個廢物了嗎?”
2008年,同為北大校友的陳生,邀請他到廣東一起殺豬賣肉。
與糾結的技術派陸步軒相比,出生于廣東湛江的60后陳生則更為活絡,他在房地產行業發家后,轉型養豬、養雞,并做起飲料。
土豬于他而言,只是合適的營銷道具之一,與其它道具并無高下之分。
也許,陸步軒也是其中一種。

某種意義上,知天命的陸步軒,已然成了壹號土豬的形象代言人。從無顏愧對社會輿論,到成為閃光燈下的直播網紅,陸步軒走過了17年。
但養豬賣肉,這個看似沒啥門檻,曾令陸步軒羞愧的行業,卻真實存在眾多高知。
10年前的雙匯生鮮品事業部主要負責人,現在的中糧肉食副總經理、當年地區的高考理科狀元,朱龍虎,便是其中一位。
07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大學生還是很稀罕的知識分子,基本都可以分配到理想公職,豬企的藏龍臥虎,充分說明它其實是一個穩定的高薪行業。
至于為什么互聯網大潮席卷而來的時候,絕大多數肉企的反應如此遲鈍與艱難,卻是與企業的文化共性密切相關。
規模越大的肉企,越有著篳路襤褸的創業過程,創始人在長期發展中的個人魅力與領導氣質越來越被神化,成為整個企業的精神導師,習慣于一言九鼎的工作作風。
而互聯網的精神,本就是平等、協作、挑戰權威,肉業的大佬們很難想象自己如馬云一樣穿著嬉皮裝上年會高歌,人家最多朗誦個《胡楊贊》或者來一支《一無所有》以樹立偉光正的形象。一人決策,萬人執行的分工,使企業的文化基因很難實現互聯網的轉型。
都說肉類加工是朝陽行業,可是朝陽行業里一樣存在沒有想象力的夕陽企業。報表上的年營收、年凈利必須逐年增長,努力狂奔的代價就是沒有空間供自己思考與轉身。
從2010年到2020年,廠家的主要產品都是那幾樣:高溫腸、低溫腸、午餐肉、鹵制品,年年如是,無趣得很。
某些頭部企業連用了幾十年的包裝圖案都不敢換,據說換了消費者就不認了,卻不知連消費者都已經換了幾代人。當然更搞笑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格的土得讓人落淚的火腿腸包裝,也能分別上演幾大品牌互相之間的抄襲,還能認真地打上好幾場官司。
與郭維世一起從伊利空降至金鑼的樊紅旺,有業界人士稱其為“肉類行業營銷第一人”,卻在這個獅子系列的包裝上失分不少,沒能充分體現“第一人”的調性。
肉企發展到行業前十,基本都已建立了強大的經銷商網絡。遍布全國的經銷商承擔了廠家與市場之間的服務功能,除了有效規避廠家的資金風險,還為客戶提供包括但遠不限于談判、配送、促銷、客情、市場推廣、余貨與退貨處理等事務,并從中獲得居間收益,而廠家也特別不把自己當外人,管理經銷商的方式通常是粗放型的激勵與罰款。
長期以來,多級經銷、區域經銷等模式的普及使廠家幾已完全依賴于經銷體系,沒有辦法對精確處理信息提供更多的資本投入,于是對市場的應對就越來越滯后,體量越龐大,反應越遲鈍。雖然有些企業成立了電商部門,那也僅僅是企業內部的一個經銷商而已;雖然也向京東淘寶等平臺供貨,那也僅僅是個供應商而已,企業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擁抱未來,只能反復防止電商平臺對傳統線下渠道的沖擊,如同歐洲大工業前期的紅旗法令。
08
2015年,萬隆開始對電商產生興趣。
他希望依托遍布全國的數萬家雙匯專賣店,構筑成包括“肉蛋奶菜糧”等品類的電商體系。
和當年冷鮮肉的引進一樣,這個想法在當時頗具前瞻性,可惜的是,企業的基因導致了這個想法仍只能停留于想法。
而同一年的3月,雙匯最大的競爭對手,隨著祝義財的失聯,開始了長達四年群龍無首的至暗時刻。
彼時雙匯剛大手筆吃下美國最大的豬企史密斯菲爾德,為了歸還收購時的巨額債務,而忙忙地在香港上了市。自此要一心一意地埋頭掙錢還債,完全沒有頭緒的電商設想就只能擱到了一邊。
當時正逢豬價上行,生鮮電商步履維艱,雙匯電商計劃的擱淺,再次說明了萬隆的英明神武、洞燭先機。
至于同一時間雙匯肉制品市場的滯漲,當然主要責任在當時的總裁——五年后雙匯雨潤搶人大戰的導火索,游牧的頭上。為什么?因為他是總裁啊。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同一年,萬隆在公司內部的經營會議上表態,禁止在企業內提及電商。他認為,電商的品質、來源是無法保證的,雙匯這么重視產品品質的企業,不可能與電商兼容,他要求各地的經銷商不得擅自將產品導入各類電商平臺,以免造成對線下傳統渠道的沖擊。
09
然而,在第二年9月,雙匯生鮮品事業部率先和京東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或許這個合作的順利達成,是因為生鮮品并不像肉制品那樣,對線下價格敏感,于是對配送要求更高的生鮮品,反而成了雙匯電商的破冰之始。
雖然舵手萬隆公開表態禁電商,但包郵區上海的業務人員偷偷把產品送到京東淘寶的店鋪去代運營,銷量相當亮眼,總部也便從善如流地過來調研取經,以準備開旗艦店,從此開啟了肉制品的電商之路。
而幾年后參股某香港連鎖餐飲集團10%,也只是為了方便向餐飲渠道供貨而已,這是不擅長服務響應的雙匯,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的渠道,至于外界媒體所稱的所謂升級版“大消費企業”則純屬過度解讀。
2017年,雙匯嘗到了“觸網”的甜頭,在京東、天貓等電商平臺上的銷量同比上一年增了了十倍,這是一個指數型的增長。
用數字說話的萬隆,不再反感電商,從善如流地將京東與雙匯的合作,升級為與萬洲國際的合作,由主管進出口業務的萬大公子主持,在紐約與劉強東聯合發布了在國內授權銷售史密斯菲爾德豬肉的戰略協議。
然而成為京東的肉類大供應商,企業就電商化了嗎?
10
2020年初,疫情洶洶而來,剛把直播玩上癮的雙匯,接著開始了極具雙匯風格的電商第三步——社區團購。
各地的業務員在朋友圈里賣力吆喝組團,成團了就讓附近的雙匯專賣店次日送到小區,團長可以分到1%—2%的返傭。
且不論習慣了10%以上返傭的團長們,對雙匯大品牌的忠誠度可否覆蓋差價,但是看得出雙匯發展電商的基本邏輯,那就是不能花錢。
這個全公司歡欣鼓舞、喜大普奔的電商入局嘗試,發生在每日優鮮、叮咚買菜等到家前置倉快速發展的同一時期,有一種特別接地氣的莫名喜感,難怪雙匯的企業畫像是中國內地淳樸的中年農民。
身家千億的大雙匯當然不差錢,投工廠投地產投設備都舍得投,電商這種務虛的東西,要花錢那就要謹慎考量了。雙匯的經營思路相當純粹,一是省錢,二是增量。傳統企業,可以理解。
11
2015年,當祝義財剛離開人們的視線,同一時期,500多公里外的漯河,雙匯大廈里,正值三年一度的雙匯經營班子換屆時期。
對于連每年長達一周的例行述職,都要全程參加的萬隆而言,這當然是件大事。
誰將是新任總裁?
消息在集團內漫天飛舞,未經確認但呼聲最高的人選是馬相杰。
當時他43歲,正是一個男性在事業期的盛年,精力與經驗最好的時候。與許多雙匯人一樣,從1996年大學畢業就來到雙匯,馬相杰與雙匯文化的契合度相當高,深受萬隆欣賞。
然而當年8月塵埃落定,當選的總裁是時年50歲的肉制品事業部總經理游牧。當時游牧從雙匯集團總經理轉任雙匯發展肉制品事業部總經理未及一年,是以又升總裁頗令雙匯人意外。

有熟悉雙匯的人推測,游牧在集團總經理職務前,已是帶領肉制品高速發展的核心高管,又在2014年9月重回肉制品后,再次令銷量大增。肉制品是雙匯最重要的部門,由肉制品領導上任總裁,一直是雙匯多年的慣例。
另有未經證實的原因之一,萬隆與新收購的美國企業的高管交流時,對方建議他,干部要到60歲才真正成熟,照此標準,彼時馬相杰顯然還過于年輕,屬于雙匯高管中的“少壯派”。
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或許并沒有意識到,中國正值數千年以來變革最快的時期,新觀念、新思維日新月異,一個敏銳通達、致力創新的帶頭人對企業的成長將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當時的雙匯已經是行業龍頭,萬隆為雙匯的發展定調為穩健,馬相杰因此成了雙匯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生鮮品事業部總經理,并在兩年之后,雙匯出現營利雙降的時期,提前出任雙匯總裁。
12
2016年起,雙匯的年會、經銷商大會的報告標題主旨,都由“大”改成了“新”。
那是萬眾創新最流行的時候,穩健發展的大雙匯也在重點搞創新,從“大進大出上規模”變成了“新時代、新征程”,并提出了“數字雙匯”的概念,相當與時俱進。
然而效果極其一般,作為企業價值長鏈擔當的肉制品的選型,依然是“老板喜歡”,促銷仍然靠囤貨壓貨,各期年報的數字都說明雙匯引以為豪的肉制品市場正在萎縮。
作為大雙匯的長子,肉制品的不給力讓萬隆著實焦急,提出了“調結構、促轉型、擴網絡、上規模”的十六字方針。
結構怎么調,轉型怎么促?一切由數據說話,以結果導向,業績上升了方向就是對的,反之就是錯的。
不得不說,雙匯真的有高手,就憑這么務虛的十六個字的指導,將相對小透明的生鮮品的占比從39%提升到61%,一躍成為公司的賺錢主力。
生鮮品的價值在于高度的流轉性,當外界議論生鮮品的盈利能力不如肉制品時,當時的生鮮品事業部老大馬相杰嘀咕:“生鮮品利潤可不低,不看我們才用多少錢啊?”

馬相杰,這位雙匯史上第一個生鮮品負責人上位的總裁,確實給萬隆帶來了驚喜。他上任之后,雙匯的業績每季度、每年都有較大增長。但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因為非洲豬瘟、貿易戰還是因為豬周期,生鮮品的屠宰量,再不復他在生鮮品任上的高峰。
可見,除了強大的能力,馬總裁真的是個好運氣的人。
13
2017年,雙匯換帥的前夜,營收、利潤雙降,卻是金鑼逆市上漲的好年頭。
這一年,郭維世大打健康牌,不僅推出“健食力”等新概念產品,還簽約了中國女排,以女排的拼搏精神與金鑼的健康生活相結合。隨著女排的屢次勝利而賺足眼球,市場大賣。
可以說,這是肉品與文體領域結合的一次成功嘗試,非常具備伊利風格的營銷特質,雙匯看后領會了相關精神,今后的幾年里,在明星、直播的娛樂道路上越走越遠。
2015年,萬隆作為隨最高領導人出訪美國的中國企業家代表團成員,坐上了西雅圖的兩國經貿談判桌,同時他又是大型美國企業的所有人,這樣的雙重身份讓記者們采訪熱情高漲。
而在國內,同樣令媒體矚目的肉類企業,則是離雙匯只有半小時車程的眾品。
那一年,總理參觀眾品,將之視為“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試點企業。當時號稱全國第四大肉企的眾品,有一個新的馬甲叫作“鮮易供應鏈”。
身材瘦小的朱獻福格局很大,十多年來,他完成了將眾品從美國的OTCBB轉板至納斯達克,又在2013年退市的壯舉,并在2014年正式向自己開刀,將傳統行業的眾品向互聯網概念的鮮易供應鏈與致力于全國物流服務的冷鏈馬甲轉型,其步幅之大,令整個社會為之側目。當時河南省交通廳還曾經下文由鮮易試行提出冷鏈物流管理的相關規范。

許昌長葛的眾品總部,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展廳,展示了鮮易與冷鏈馬甲的發展規劃。
雖然可以熟練講解鮮易供應鏈O2O模式,可朱獻福其實并不真懂互聯網。摸著石頭過河,眾品勇氣可嘉,可是盈利邏輯不清晰,并指望政府投入資金啟動的鮮易,所講述的故事最終并沒有得到資本市場的認可。
眾品不斷發行債券,并在之后試圖重組香梨股份,結果均未成功,讓想試水做電商但尚未下手的同行們都暗呼好險。
但生鮮電商的蓬勃發展說明,不是生鮮電商不行,只是你的生鮮電商不行罷了,時機未到并不是唯一的理由。
14
倒在2019年豬周期前夜的豬企,不僅僅是眾品,另外一家著名的企業,是同在河南的雛鷹農牧。
雛鷹農牧的創始人侯建芳從1988年養豬開始,至2010年成為“中國養豬第一股”,然后在2019年10月黯然退市,成為“養豬退市第二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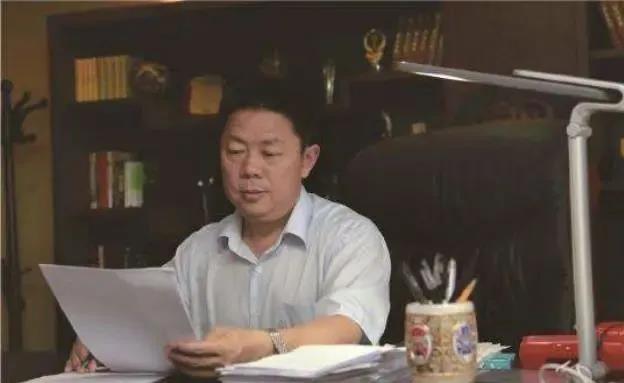
侯建芳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心路歷程,可能是發現養豬來錢太慢,遠不如做金融。那是非洲豬瘟陰影下的至暗時刻,雛鷹農牧質押了大量股權,進入了包括電競在內的各種產業。
最后,退市公告中表示,雛鷹的豬由于沒錢買飼料,餓死了。與當年同期的獐子島扇貝一樣,成為不明原因集體失蹤的物種。
侯建芳的落幕,讓同省的老鄉秦英林,成了千億級的獨孤求敗,真是江湖寂寞啊。
2018年的貿易戰,2019年的非洲豬瘟,2020年的新冠疫情……近幾年,一只只黑天鵝與灰犀牛共同助推了2020年的豬周期高位,一早買不起房的國民愕然發現,現如今竟然連豬肉都吃不起了。
養豬股一飛沖天,殺豬股也不遑多讓,股市的狂歡之下,是各大豬廠屠宰量、分割率越來越低的事實。
而這又是一個生鮮到家電商迅速發展的時刻,僅上海的叮咚買菜,疫情期間,就日銷氣調豬肉十多萬盒,同一賽道的,還有盒馬鮮生、每日優鮮等前置倉企業。由于配送即時到家的鮮品,這些企業已在業態上優于次日送達的興盛優選等社區團購,更優于送貨時長更久的京東、淘寶等傳統電商。
更快所以更強,電商的優勢邏輯并不基于規模大小,在這一場變革中,氣調小包裝已經優于適合凍品的真空裝,這對廠家的即時反應能力、市場服務能力、即配冷鏈能力與切割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5
中糧是眾所周知的大國企,中糧肉食在同行業中卻是個小個子。然而規模不算大卻有著大國企的胸襟。
疫情最兇險的時刻正值春節假期,身在疫區中心的武漢中糧肉食,全體員工冒著生命危險堅守崗位,為市民保障供應,是當時當地唯一開工供貨的肉企。疫情期間,中糧肉食向各區域電商平臺,每日提供了數十萬盒小包裝氣調產品。
在規模遠比它大得多的肉企都限制分割量盡量減少虧損,做進口分割掙錢的2020年,中糧肉食始終保持精分割的品質,將小包裝氣調產品做得風生水起。
雖然氣調包裝設備不是最新的,但積累了十多年的精分割技術團隊與管理制度卻是其獨有的核心競爭力,在分割越細越虧錢的今天,支撐他們占領新市場的,是從飼料開始的養殖屠宰一體化全產業鏈。
今年,許多賺到盆滿缽滿的養豬企業紛紛入局屠宰,或許也是基于相似的邏輯,牧原、新希望紛紛擴大養殖配套屠宰廠。
只是,工業化的積累非一朝一夕之功,并不是挖一兩個現成的熟手,建個廠房,買個設備就能做到。企業經營管理的精髓,很難復制照抄,需要自己全程走過。
16
2019年1月,消失1400天的祝義財,歸來。
甫獲自由,老父親已逝世近兩年,面對老父親的靈柩,祝義財聲淚涕下,“雖然萬萬不得已讓您在這冰冷的殯儀館等了太久、太久,但終是逝者為大、入土為安。在您彌留之際,不孝兒子大逆不道沒能在您老人家身邊送終盡孝,對不起!不孝兒子祝義財在這里給您重重磕頭,對不起!懇求您理解兒子的萬般無奈。”
短短數月后,祝義財又再次告別了母親,“今年元月份我回到南京后,先是送走了在冰冷的殯儀館久久等待的老父親;時隔八個月,我的老母親又永遠的走了。在我人生最困難的階段,父母雙雙離去,這讓我悲痛欲絕、不能自已。”
曾經輝煌的企業,已經輝煌不再。失去自由前,他的多項戰略布局,又錯失了黃金時間。
給他的補償,或許值一個雙匯吧,然而并沒有。
雨潤位于南京,這個六朝古都雖是龍脈所在,卻總有些末世王朝的意味。
現在的祝義財正當盛年,仍然有東山再起的意志與實力,雖然外界不一定看得懂他的招式。例如,無情逼走四年間勉力支撐公司運轉的高管們,過早將自己的子女列入權力中心。
或許,至親的不斷離開,讓此時的祝義財更加珍視,也只相信骨肉親情。
這四年,影響肉企發展的因素太多,但如今雨潤大力進軍高溫市場,并且決定把商超的直營模式改回經銷模式的市場策略,總讓人想起“不做大哥很多年”的老大哥,珍而重之地挖出珍藏的BP機準備重出江湖的電影片段。
是眼光獨到,還是刻舟求劍,自有市場最終給出正確的評判。
與雨潤未來的發展走向相比,吃瓜群眾喜聞樂見的是,游牧任職雨潤之后引發的雙匯員工辭職潮。較為有趣的是,有幾個業務人員離職手續未辦完,即遭任命,于是被扣了下來,并被要求公開喊麥“我不是我沒有我是被逼的。”
雙匯一直有把危機公關處理成鬧劇的喜慶基因,但由于這次行為藝術的規模太大,讓業內廣大吃瓜群眾都差點忽略了另一個大瓜——新希望80后張明貴接任鄧成的總裁之位,而鄧成已赴任天邦股份董事長。
17
2020年的疫情,不僅與豬肉密切正相關,還引發了高科技產業的芯片戰爭。當任正非老父親四處為女兒吶喊的時候,芯片的概念隨著愛國主義情懷在國內空間高漲。此時,新希望的劉永好提出了“豬芯片”的理論。
劉永好認為,種豬就是豬的芯片,中國現在最為普及的外三元種豬均由國外引進,生出第四代后就不能再繁殖而必須繼續進口種豬,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帝國主義會趁機扼住我國民眾貪吃的脖子。

這樣的吶喊確實振聾發聵,然而目前并沒有好的引導方案。現在普及的豬種,本就是國內市場與消費習慣的選擇,所有的肉企都不可能以飽滿的情懷,囤上一圈子賣不動的本地肥豬,包括新希望自己。
那么劉永好的焦慮,或許更多來自于企業發展的瓶頸,從產業到產業鏈到全產業鏈,接下來,它的方向在哪里?回溯源頭做種豬?跨界供應做牛奶?或者干脆完全轉型去蓋房子?
雖然劉暢已經完全接班,仍然有劉永好憚精竭智的思考為其保駕護航。
18
從2010年到2020年,是中國肉業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
放眼所見,肉企的成功,是時代賦予的成功,消費升級、經濟發展,讓人口最多的中國吃掉了世界上一半的豬肉;
而肉企的失敗,應該說,是價值觀的失敗。價值觀無所謂對錯,卻有可能過時,再不是“麒麟擇主,可安天下”的個人英雄主義時期。
2020年著名的瑞幸咖啡事件之后,一位著名的生鮮電商企業創始人曾如是說:
“因為一個事件而粗糙地否定一個賽道,否定一種商業模式,是思考上的懶惰。一個相同的賽道,有不同的商業模式,差之毫厘,謬之千里,而結局也有天壤之別。
一個公司的失敗有多種原因,有人杠桿過度,有人精力分散,有人年少輕狂,有人急于求成,有人驕奢失志,各不相同,其實根本原因大多都是敗于價值觀出錯,自我太大。
如果你能堅持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創始人第四,你即使無法大成,一般也能善終。如果創始人把自己的排序提到前面,一般噩夢就會自動開啟。
什么是堅持?什么是執念?為他要,是堅持;為我要,是執念。這是反人性,所以特別難,共勉。”
時光匆匆如逝水,十年彈指一揮間。
萬隆、祝義財、劉永好、明金星、秦英林、朱獻福、陳生、陸步軒、郭維世、游牧、馬相杰、朱龍虎、劉暢、侯建芳……
他們,有的是創始人,有的是經理人,有的是接班人;有的獲得成功,有的遭遇挫折,有的東山再起。
但共同的是,他們都用盡心盡力的思考與工作,為中國肉業奉獻出了自己最動人的芳華。
走過高峰,也可能行過低谷,在這個存量極大的朝陽行業里,見宇宙之大,天地之遙,江湖之遠,個體之微,未到蓋棺之時,均難掩卷說勝負,且將行路,當作修行,風起四海,各安天涯。






